男女主角分别是鲁迅武大郎的女频言情小说《伴我半生:一个人的微阅读鲁迅武大郎全文免费》,由网络作家“侯德云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鲁迅的微型小说《一件小事》,我怎么看,都觉得是另类。是鲁迅小说中的另类。其中有让人生疑的人性亮点,也有硌人眼球的自我反省,看起来特别不像出自鲁迅之手。我这样说,理由有两个:其一,鲁迅作品中的人性亮点,极少见;其二,鲁迅的自“我”反省,哪怕是虚拟的自“我”反省,也极少见。《一件小事》的亮点,聚焦在人力车夫身上,也就是当年所说的“普罗大众”身上,用现在的话说,是在“低端人群”身上。而主动反省的那个“我”,则是有钱阶层,属于穿得起皮袍的高端人群。你瞅瞅这里边,是不是有点阶级的意味?故事简单到疑似一篇中学生记叙文的模样。民国六年冬天,“大北风刮得正猛”,一个穿皮袍的人,出门叫了人力车,赶往“S门”。途中,一个穿着破烂、头发花白的老女人,“从...
《伴我半生:一个人的微阅读鲁迅武大郎全文免费》精彩片段
鲁迅的微型小说《一件小事》,我怎么看,都觉得是另类。是鲁迅小说中的另类。其中有让人生疑的人性亮点,也有硌人眼球的自我反省,看起来特别不像出自鲁迅之手。我这样说,理由有两个:其一,鲁迅作品中的人性亮点,极少见;其二,鲁迅的自“我”反省,哪怕是虚拟的自“我”反省,也极少见。
《一件小事》的亮点,聚焦在人力车夫身上,也就是当年所说的“普罗大众”身上,用现在的话说,是在“低端人群”身上。而主动反省的那个“我”,则是有钱阶层,属于穿得起皮袍的高端人群。你瞅瞅这里边,是不是有点阶级的意味?
故事简单到疑似一篇中学生记叙文的模样。
民国六年冬天,“大北风刮得正猛”,一个穿皮袍的人,出门叫了人力车,赶往“S门”。途中,一个穿着破烂、头发花白的老女人,“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”,车夫让开道,老女人的破棉背心没系扣,兜到车把上,被拽倒了。是“慢慢地倒了”。
皮袍客料定老女人没有受伤。老女人却对车夫说:“我摔坏了。”
皮袍客心说:“我眼见你慢慢倒地,怎么会摔坏呢,装腔作势罢了,这真可憎恶。”
车夫却是“毫不踌躇”,搀着老女人,往“巡警分驻所”走去。那个分驻所,大约等于交通支队之类的单位吧。
就在这时,皮袍客看着车夫和老女人远去的背影,脑子里突然开始打雷,精神境界咔嚓咔嚓地逐渐升华起来:他竟然看见车夫的背影越走越高大,“须仰视才见”,同时还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向他压榨下来,要“榨”出他藏在皮袍下面的那个“小”。
好,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其实我不讲,大家也都熟悉,都在初中语文课本上“学”过嘛。
现在我们回头,用理性,把故事情节再捋一遍,看看能捋出什么东西。
我捋了一下,很快捋出一些疑点。
其一:老女人“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”。这行为,不就是近年来屡屡发生的碰瓷吗?
其二:我跟皮袍客想的一样,慢慢倒下,怎么会摔坏?碰瓷才会说“摔坏”对不对?
其三:按常情常理,验证老女人是不是真摔坏了,或者打算给她治疗,都应该送她去医院,干吗要送交通支队?车夫的行为,有悖于常情常理。
其四:车夫把顾客扔在道上,连句客气话都不说,是不是不近人情?
其五:为什么是巡警出来告诉皮袍客,说车夫不能拉他?车夫自己不出来,是被老女人揪住不放还是怎么?嗯?
我使出很大力气,想找到让皮袍客脑子里打雷的前因。可惜找不到。使劲找也找不到。为什么要打雷?很奇怪嘛,像车夫不送老女人去医院一样奇怪。
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皮袍客之腹。没法子。老侯的精神境界就这么矮,比武大郎还矮,怎么提,都提不上来。
说起来,还是人家皮袍客更让人心热,“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圆”,让巡警转交车夫。这个细节,是鲁迅刻意要让我们看到,打雷不能白打,皮袍客的灵魂深处已经发生了革命。
有人说《一件小事》是一篇“幼稚的记叙文”。你咂摸咂摸,这话是不是有点道理?
《鲁迅年谱长编:1881—1921(第一卷)》记载,《一件小事》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《晨报·周年纪念增刊》。收入小说集《呐喊》时,鲁迅在篇末误记为1920年7月20日。这个错误,一直错到现在。鲁迅的错,谁都“不舍得”纠正,说起来也是比较奇怪。
我特别想说的是,鲁迅的小说,在《一件小事》前后,都以揭示人性的阴暗为己任。无论是《孔乙己》《药》,还是《故乡》《阿Q正传》《祝福》,都一样。连曾经那么诗意的少年玩伴闰土,成年后也被奴性所束缚。“豆腐西施”杨二嫂更惨,浑身都是流氓性。
鲁迅不会看你是底层,是草根,是“低端人群”,就放过你身上的劣根性。他才不会,他是“一个都不饶恕”的人。毕飞宇说得好,鲁迅他阴,他刚,他冷,他的小说,肩负着“启蒙”的伟大使命。
可鲁迅偏偏把一抹阳光打在人力车夫的背影上,甚至不惜跟生活逻辑对立,执拗地把思维正常的皮袍客,弄得很“小”。
鲁迅在《一件小事》的结尾段落,说“几年来的文治武力”像他小时候读过的“子曰诗云”一般,都忘了。唯独发生在“民国六年”的这件小事,“总是浮在”眼前,“有时反更分明”,想忘也忘不掉。
看来鲁迅是受到了某种刺激。“几年来的文治武力”,借他本人的话说:“见过辛亥革命,见过二次革命,见过袁世凯称帝,张勋复辟,看来看去,就看得怀疑起来,于是失望,颓唐得很了。”
鲁迅果然是受了刺激,对穿皮袍的高端人群感到失望,一念之差,才有了这篇让后人反复误读的作品。
我注意到百度百科对《一件小事》的过分解读:“一般人只会把它看作是一曲人力车夫正直无私品德的颂歌,而不会将之上升到赞扬劳动人民,提倡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”的精神高度。
你瞅瞅人家百度百科说得多好,跟我们当年中学语文教学中的“标准答案”几乎一模一样。
延伸阅读:
一件小事
鲁迅
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,一转眼已经六年了。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,算起来也很不少;但在我心里,都不留什么痕迹,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,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,—老实说,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。
但有一件小事,却于我有意义,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,使我至今忘记不得。
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,大北风刮得正猛,我因为生计关系,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。一路几乎遇不见人,好不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,教他拉到S门去。不一会,北风小了,路上浮尘早已刮净,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,车夫也跑得更快。刚近S门,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,慢慢地倒了。
跌倒的是一个女人,花白头发,衣服都很破烂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;车夫已经让开道,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,微风吹着,向外展开,所以终于兜着车把。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,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,跌到头破血出了。
伊伏在地上;车夫便也立住脚。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,又没有别人看见,便很怪他多事,要自己惹出是非,也误了我的路。
我便对他说:“没有什么的。走你的罢!”
车夫毫不理会,—或者并没有听到,—却放下车子,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,搀着臂膊立定,问伊说:
“你怎么啦?”
“我摔坏了。”
我想,我眼见你慢慢倒地,怎么会摔坏呢,装腔作势罢了,这真可憎恶。车夫多事,也正是自讨苦吃,现在你自己想法去。
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,却毫不踌躇,仍然搀着伊的臂膊,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我有些诧异,忙看前面,是一所巡警分驻所,大风之后,外面也不见人。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,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。
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,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,霎时高大了,而且愈走愈大,须仰视才见。而且他对于我,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,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来。
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,坐着没有动,也没有想,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,才下了车。
巡警走近我说:“你自己雇车罢,他不能拉你了。”
我没有思索地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圆,交给巡警,说:“请你给他……”
风全住了,路上还很静。我走着,一面想,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。以前的事姑且搁起,这一大把铜圆又是什么意思?奖他么?我还能裁判车夫么?我不能回答自己。
这事到了现在,还是时时记起。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,努力地要想到我自己。几年来的文治武力,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“子曰诗云”一般,背不上半句了。独有这一件小事,却总是浮在我眼前,有时反更分明,教我惭愧,催我自新,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。
贾大山的《莲池老人》让我有了一种恋爱般的感觉。
我爱的是莲池老人幽默达观的处世哲学。我爱的是贾大山流畅自如像山泉一样清凉明净的语言品质。我爱这篇作品中疏朗散淡的禅机和自然情趣。
现实的人生境况,古典的诗意,在《莲池老人》中和睦共处。
莲池老人在小说中的“亮相”,是一幅意境悠远的中国传统山水画。不是工笔,是小写意:
寺院的山门殿宇早坍塌了,留得几处石碑,几棵松树,那些松树又高又秃,树顶上蟠着几枝墨绿,气象苍古;寺院的西南两面是个池塘,清清的水面上,有鸭,有鹅,有荷;池塘南岸的一块石头上,常有一位老人抱膝而坐,也像是这里的一个景物似的。
随着叙述的伸展,我很快又看到了一幅田园风情图:
他又在自己的院里,种了一畦白菜,一畦萝卜,栽了一沟大葱。除了收拾菜畦子,天天坐在池边的石头上,看天上的鸽子,看水中的荷叶……
汪曾祺在《晚饭花集》自序中说:“我写的人物都……是我每天要看的一幅画。这些画幅吸引着我,使我对生活产生兴趣,使我的心柔软而充实。”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手法在这里不期而遇。我们从这种不期而遇中悟到了什么?
我相信,贾大山在塑造莲池老人这个小说人物的时候,他的内心也一定“柔软而充实”。
莲池老人负责看护寺院里的钟楼,每月从文物所领取四元钱的补助。这点钱实在微不足道,但他好像对此并无怨言,把“一畦白菜,一畦萝卜”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也许,真的是池塘边的清风明月、水气荷香给了他一种非同凡响的“功夫”。这种“功夫”让他看破尘嚣,知足常乐。在买电视的问题上,在“抢占宅基地”的问题上,他的一言一行,都让我们忍俊不禁,但又不能不赞同他的观点和做法。这是一个真正理解了生活又懂得怎样生活的人。
我希望生活中能多一些莲池老人,这样的人多了,我们的生活就会少一些浮躁;我希望文坛上能多一些贾大山,这样的作家多了,我们的文学就会多一些纯真。
老作家孙犁说贾大山的作品“是一方净土……是作家一片慈悲心向他的信男信女施洒甘霖”。这无疑是一句真知灼见。
我敬佩莲池老人。我更敬佩贾大山。
反复阅读《莲池老人》,使我确信:有一种作品,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欣赏,品味。反复阅读《莲池老人》,同时也使我确信:有一种作家,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向他表达由衷的敬意。
当代笔记小说,阿成是不容忽视的存在。
很多作家都是名不副实的,要么被高估,要么被低估。阿成也一样,也名不副实。他是被低估的作家。当然,高估低估,要看跟谁比……
这是题外话,不说也罢。咱们接着说阿成的笔记小说。
这回,说说他的《刀削面》。这篇作品,也可以排列在微型小说阵营。
《刀削面》的开头和结尾,都看似随意——阿成很多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看似随意——从读者角度来看是随意,对作者本人而言,却是精心构思而成。
先说开头:“在奋斗路那儿,有一家大同面食馆,我常领着老婆孩子去那儿吃一顿。”说完这句,阿成立刻把话题荡开,说别的,说领着老婆孩子去“台中牛排馆”吃饭的事,很详细,用了六个自然段。
“台中牛排馆”是自助餐,品种很多,各种肉,各种蔬菜,各种炒菜,各种甜食,各种主食,各种饮料,价格四十八元一位。在作者看来不算贵,何况,家人可以吃得比较自由些。结果呢,吃得倒是比较自由,可家里人都“认为贵。太贵!”。
于是领着家人去大同面食馆,吃山西风味的刀削面。
然后,话题再次荡开,说他“年轻的时候,就喜欢吃山西刀削面”。说起八角街一个不大的面馆,“一大锅沸开的水,大师傅娴熟而惊险的削面技术,嚓嚓嚓,削得薄而利落。”你瞅瞅他观察得多细!做法说完,说吃法,“加老醋、加蒜末,加一点酱油”,吃出“一额的汗”,上瘾了,常去吃。随之不经意地跟汉堡包做了比较,后者“黏不叽的,咬在嘴里,有一种被洋人调戏的感觉”,每次吃,也还是觉得贵。
看到这里,我笑了。我对汉堡包的感觉,跟阿成一样一样的。知心人哪。
这个环节阿成也说得详细,用了五个自然段。
然后,又说某年在天津吃刀削面的事。不是他自己,还有几位工友。路上看见刀削面馆,阿成要吃,别人都反对。“有大菜馆吃这东西干什么?”之后是阿成吃,别人看,然后是跟工友的对话。
这一碗刀削面吃得有些尴尬,差点跟工友之间把关系闹僵,“一路上大家半天没说话”嘛。
你瞅瞅阿成,为了一碗刀削面,啧啧。
最详细的叙事,发生在北京。阿成和文友老邱——老邱嘛,我认识。如果可以对号入座的话,不光认识,还一起玩过喝过聊过,挺逗的一个人,还直率——阿成的小说,有些环节是可以当真的,有些不可,不过我很愿意相信,发生在老邱身上的事,是真的。
哥俩好长时间没见,老邱要请饭,阿成说,一碗刀削面。老邱不干,“那不扯呢吗?那叫啥呀?”但阿成再三坚持,于是颇费周折,在一家大商场的顶层吃上了刀削面。
阿成的坚持,一定让老邱觉得一阵阵犯糊涂。但我能理解。有时候,一口饭,跟一个人,有共通之处。你见一个人,有时千山万水的,还总是情哩,吃一口饭,怎么就不可以费些周折?怎么就不是情呢?
我想现在该做个小结,拢拢思绪。小人物的生活,大抵如此的吧:情系物美,更要价廉。刀削面对于阿成,对于阿成笔下的“全家”就是这样。
有人总结说,国人最爱听的词汇,有两句,一句是“打折”,另一句是“免费”。呵呵。难怪骗子总最喜欢用这两个词汇构筑陷阱。
《刀削面》的结尾是神来之笔。还是那家大同面食馆,阿成与小女儿在吃面,看见一对母女走进来,女儿十四五岁,“她们选了一个小桌坐下”,“只要了一碗刀削面”,“女儿吃着,说着”。
最揪心的一句话,是“母亲坐在对面,静静地看着”。
一碗刀削面,女儿吃,母亲看,而且是“静静地看”。这里边,会不会暗藏了一个让人伤感的故事呢?
阿成肯定感觉到了什么,“慢慢地流下了眼泪”。
小人物的生活,大抵如此的吧,难免遭遇一些些伤感的故事,也止不住为这样的故事洒些同情的泪水。
阿成以刀削面为把手,向我们表达了人与食品之间,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。这样的精品佳作,在笔记小说之林,在微型小说之林,都不多见。
很久了,有六七年的时间,我一直在寻找鲍昌。我寻找的是微型小说的鲍昌。
终于找到一份介绍鲍昌的短文,第一句是这样说的:“中国当代作家,生于1930年,卒于1989年。”他的短篇小说《芨芨草》在1982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,而那时候,老侯还是一名乡村中学的学生,根本没听说这件事。他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庚子风云》,我也不曾读过。简介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:“晚年曾专门致力于小小说创作,发表了一批质量很高的小小说作品。”可这批“质量很高”的小小说或叫微型小说躲到哪里去了呢?我查阅了很多出版物,只找到《琴怨》《未了的债》等屈指可数的几篇。
如果不是有幸读到了《琴怨》,那个名叫鲍昌的人,肯定会被一些信息的灰尘埋没在我的记忆之中。
《琴怨》是一首婉约的诗。它又像是一首小提琴曲,为我们演奏挥之不去的浓郁的忧伤。那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忧伤。
小说的背景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时代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疯狂遮盖着人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惧。在这个时候,一个年方十九,需要照顾两个弟弟的女孩子,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寄托给了琴声的悠扬。
“一年以后,那琴声就宛如江上之歌吹、谷中之林籁。他觉得:琴声也有情呢,琴声也有色的。是踩碎花瓣的游春女儿之情;是绿草湖边朝霞的颜色。”
这是极度苦闷之中短暂的欢乐,是划破心灵夜空的闪亮的流星。
“给我拉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曲子吧!”
这是爱情的萌动,是一场“蝴蝶织成的没有挂牵的梦”。
“叶老师应该知道:我太苦了,没有人爱我。”
“遗书”里的这一声表白,是那位少女对整整一个时代的控诉,类似于乐曲中骤然而起的高潮,让另一个时代的良心微微发颤。
这篇微型小说的结构值得我们注意。它不是以时间的顺序,而是以记忆的顺序、抒情的顺序结构而成的。它淡化了情节,以诗的因素融贯全篇。它的韵味是醇厚的,有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朦胧。
我总觉得《琴怨》是用小说的形式写成的诗。它拥有很强的艺术个性,这种艺术个性会帮助它抵御时间漫长的风化。它为我们指出了一种结构的方向,也指出了一种意境的方向,同时也有力地展示了作者主体构想上的独断专行。
“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,都必须浸透作者的人格和感情,想达到这个目的,写作时要独断,彻底的独断!”我们应该牢记沈从文先生的教导,像鲍昌那样独断专行地开辟自己的文学道路。
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,还没有发现哪位中国当代作家比汪曾祺先生更看重小说的语言问题。他在《小说笔谈》一文中,用了一个小节的篇幅专门谈论小说语言的“叙事与抒情”。他说:“现在的年轻人写小说是有点爱发议论。夹叙夹议,或者离开故事单独抒情。这种议论和抒情有时是可有可无的。”他说:“一件事可以这样叙述,也可以那样叙述。怎样叙述,都有倾向性。”他说,倾向性不需要“特别地说出”。怎样表现倾向性呢?“中国古语说得好:字里行间。”在这篇文章中,汪曾祺先生还告诉我们,一个小说家,要懂得“在叙事中抒情,用抒情的笔触叙事”。
让我们一起阅读汪曾祺先生的微型小说名作《陈小手》。
陈小手满头大汗,走了出来,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:“恭喜恭喜!母子平安!”男主人满面笑容,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。陈小手接过来,看也不看,装进口袋里,洗洗手,喝一杯热茶,道一声“得罪”,出门上马……
在这段叙述之中,我看见汪曾祺先生向陈小手投去的是一缕赞赏的目光。“看也不看”,暗示了陈小手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。汪曾祺先生赞赏的正是陈小手的豁达。接下来一句,“陈小手活人多矣”。除了加大赞赏的浓度之外,汪曾祺先生在这里还预先表达了对陈小手不幸身亡的惋惜与同情,也预先表示了对“团长”骄横跋扈草菅人命的愤恨。
团长的太太(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),要生了,生不下来。叫来几个老娘,还是弄不出来。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。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。
括号里的一句“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”,意味深长,它表达了汪曾祺先生对“团长”的冷漠,到了“弄不出来”,“杀猪也似的乱叫”,作者的情感渐渐从冷漠上升到厌恶的程度。然而叙述还在延伸:
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,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。
“脂油”和“掏”是厌恶的继续,也是作者倾向性的继续。汪曾祺先生没有对“团长”和“团长太太”发表一个字的议论,但他的主体情绪已经毫无保留地抒发出来了。他是怎样抒情的呢?—“字里行间”。
《陈小手》完成了汪曾祺先生“叙事与抒情”理论的实践阐述,为我们指出了小说语言的方向。这是一笔永恒的文学遗产,可以让每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享用终生。
汪曾祺先生在谈到微型小说的时候曾经说过,微型小说“要做到字字珠玑,宣纸过墨不能易之,一个字不能改”。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。我终于认识到,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绝句,微型小说作家必须像唐人写绝句一样去锤炼作品语言才行。这是拯救微型小说唯一的途径。
我的朋友王海椿对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也情有独钟。他对我说:“汪曾祺写得从从容容,初读似乎平淡,细细品味之后,不禁拍案叫绝:有味!”
能说出这样一番话的人,他身上一定饱含着优秀作家所特有的品质。王海椿后来果然成为一个优秀的微型小说作家,他以《雪画》《大玩家》《大家子弟》等诸多优秀作品而闻名全国。
有志于微型小说创作的文学爱好者,甚至包括一些当红的微型小说作家,都应该好好学习汪曾祺先生的小说语言。写到老,学到老,直到自己笔下的作品“字字珠玑,宣纸过墨不能易之”。
延伸阅读:
陈小手
汪曾祺
我们那地方,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。一般人家生孩子,都是请老娘。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,差不多都是固定的。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、二少奶奶、三少奶奶,生的少爷、小姐,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。老娘要穿房入户,生人怎么行?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,哪个年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,当“抱腰的”,不须临时现找。而且,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“吉祥”,接生顺当。—老娘家供着送子娘娘,天天烧香。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?—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,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,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人。她也不会接生,只会看内科,是个老姑娘。男人学医,谁会去学产科呢?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,不屑为之。但也不是绝对没有。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妇科医生。
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,比女人的手还小,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。他专能治难产,横生、倒生,都能接下来(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)。据说因为他的手小,动作细腻,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。大户人家,非到万不得已则不会请他的。中小户人家,忌讳较少,遇到产妇胎位不正,老娘束手,老娘就会建议:“去请陈小手吧。”
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,但是都叫他陈小手。接生,耽误不得,这是两条人命的事。陈小手喂着一匹马。这匹马浑身雪白,无一根杂毛,是一匹走马。据懂马的行家说,这马走的脚步是“野鸡柳子”,又快又细又匀。我们那里是水乡,很少人家养马。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,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“马队”,觉得非常好看。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,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,称之为“白马陈小手”。
同行的医生,看内科的、外科的,都看不起陈小手,认为他不是医生,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。陈小手不在乎这些,只要有人来请,立刻跨上他的白走马,飞奔而去。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,立刻就安定了一些。他下了马,即刻进了产房。过了一会儿(有时时间颇长),听到哇的一声,孩子落地了。陈小手满头大汗,走了出来,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:“恭喜恭喜!母子平安!”男主人满面笑容,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。陈小手接过来,看也不看,装进口袋里,洗洗手,喝一杯热茶,道一声“得罪”,出来上马,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“哗棱哗棱”……走远了。
陈小手活人多矣。
有一年,来了联军。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,是两支军队。一支是国民革命军,当地称之为“党军”;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。孙传芳自称“五省联军总司令”,他的部队就被称为“联军”。联军驻扎在天王庙,有一团人。团长的太太(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)要生了,生不下来。叫来几个老娘,还是弄不出来。这太太杀猪也似的乱叫。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。
陈小手进了天王庙。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“走柳”,见了陈小手,说:“大人,孩子,都得给我保住,保不住要你的脑袋!进去吧!”
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,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。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,累得他筋疲力尽。他迤里歪斜走出来,对团长拱拱手:“团长!恭喜您,是个男伢子,少爷!”
团长龇牙笑了一下,说:“难为你了!—请!”
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。副官陪着。陈小手喝了两口。团长拿出20块大洋,往陈小手面前一送:“这是给你的!—别嫌少哇!”
“太重了!太重了!”
喝了酒,揣上20块现大洋,陈小手告辞了:“得罪!”
“不送你了!”
陈小手出了天王庙,跨上马。团长掏出手枪来,从后面,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。团长说:“我的女人,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!她身上,除了我,任何男人都不许碰!你小子太欺负人了!日他奶奶!”团长觉得怪委屈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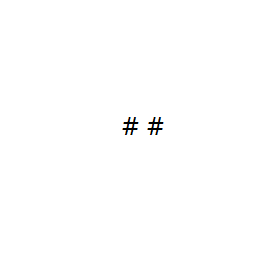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